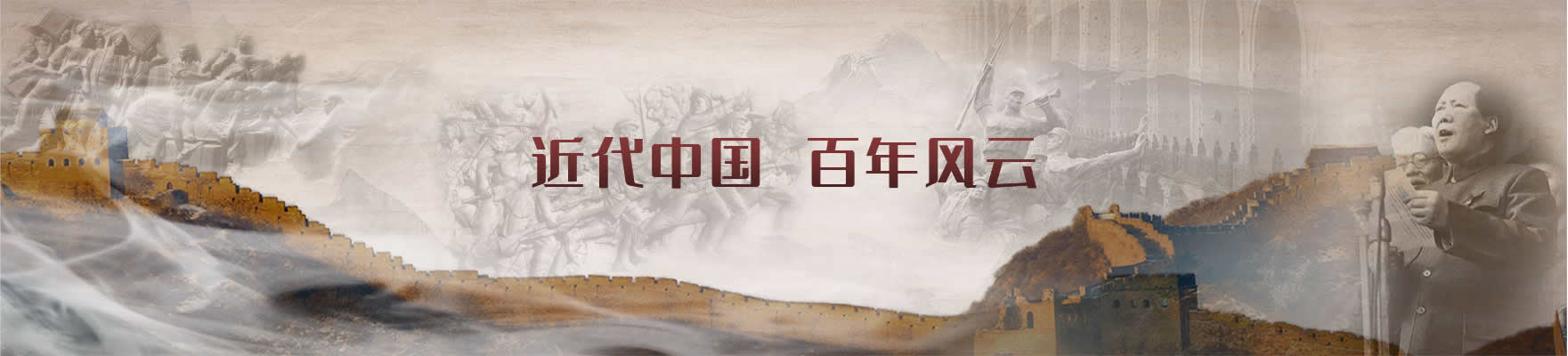【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对东北军实行整编。然而,整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国民政府拆散西北“三位一体”联盟,将东北军东调豫皖苏,为实现整编创造条件。同时,国民政府坚持将东北军直隶中央,反对张学良、于学忠等人继续统率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强硬要求下,东北军新一一〇师被解散,一二九师经东北军各将领协商,获得妥善安置。东北军的整编有利于国家的抗日准备,因而得到中国社会舆论的普遍肯定,直接反映出西安事变后对内团结息争、对外抗日御侮已经成为主流民意。
【关键词】
东北军 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1935年起,随着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加深,国民政府开始加紧进行抗战准备,抗战战略转向积极。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在军事方面,对地方实力派军队的整编构成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国民政府对刘湘统率的四川军队开展的川康整军,对东北军的整编则关注不足。有关东北军的论著虽然对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多有提及,但均未进行深入探讨与全面考察。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同时参酌其他相关文献,对西安事变后至卢沟桥事变前的东北军整编问题进行详细梳理与考察,以期深化东北军研究,丰富今人对于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认识。
一、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东调豫皖苏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但是,张学良到南京后旋即被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随之开始。
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划分陕甘地区国民党中央军、杨虎城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驻地,规定东北军各部一律恢复1936年12月1日以前原位置。1月6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陕甘军事善后方案》提出补充办法,要求“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国民政府要求东北军向西集中驻扎甘肃,目的是使东北军尽快让出西安和关中,以便中央军进驻,掌控西北局势。
然而,1月7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函电中提出两种不同情况下东北军的调派方向。若国民政府继续“剿共”,则“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如国民政府放弃“剿共”,则“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此时,张学良的主张背离了西安事变爆发前与十七路军、红军三方联合,建立所谓“三位一体”的共同利益。张学良的动机与意图是设法解除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怀疑而使自己获得自由。稍后,蒋介石参酌张学良意见,拟定甲、乙两案,供西安方面择一执行。甲案规定,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乙案规定,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集中于南阳、襄樊、信阳一带。甲案是西调方案,乙案是东调方案。
但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方案并不满意。1月16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新的方案。该方案不仅提出释放张学良回陕西和中央军撤退等要求,而且也隐含排除国民政府势力、继续维持西北“三位一体”之半独立局面的意图,等于完全否决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方案,自然招致南京方面的反对。1月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痛斥其方案“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蒋介石明告杨虎城三点:第一,“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第二,关于张学良回陕问题,“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第三,“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张学良亦反复劝说杨虎城接受甲案。在内外压力之下,杨虎城同意执行甲案,并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潼关展开谈判。经过复杂、艰难的交涉,杨虎城终于决定从前线撤兵。
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元老派、少壮派之间围绕营救张学良问题出现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分歧,酿成二二事件。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主张先从前线撤兵,再谋求营救张学良。与之相反,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则坚持先营救张学良回陕,甚至不惜为此与中央军一战。少壮派将营救张学良和从前线撤军两事完全对立,不愿在未救出张学良的情况下遽然撤军。他们非常清楚,如欲实现“先救张”的目标,必须设法排除来自元老派的阻碍。当少壮派“清楚地听到主和决定时……简直不能容忍,认为这几个主和的人是他们主战的阻力,不除去这几个人,一切都完了”。在这一偏执思维的主导下,少壮派决定铤而走险,杀掉主和的王以哲等人。2月2日,少壮派枪杀王以哲,坚持不撤兵,意图营救张学良。
但是,二二事件不仅未能实现少壮派的既定目标,反而引起元老派的激烈反弹。二二事件发生后,元老派展开肃军行动,赞成甲案的少壮派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如此,二二事件还使元老派丧失对中国共产党和杨虎城的信任,动摇了“三位一体”内部的关系基础。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元老派转而倾向于执行乙案。2月5日,元老派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在高陵共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乙案,东北军开出潼关。2月14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致电蒋介石、何应钦,也提到“东北军各部均不愿西调,最好东调,调防时可由一〇五师及六十七军开始”。陈诚认为,“中央如能充分体察其下情,因势利导,示之以信而安其心,则将东北军分别东调陇海平汉津浦各路,非不可能”。
此时,中共非常希望东北军执行甲案,继续留在陕甘地区,维持“三位一体”之存在。2月4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2月1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分析蒋介石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分化政策,建议我党应采取的对策是:团结东北军,促其全部开入甘肃境内,避免被蒋介石分割;巩固和训练十七路军现有部队。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2月24日,缪澄流告知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一、杨赤两方不时派员赴东北军各部勾煽离间,极力反对单独东开;二、彭德怀致缪、刘养午电,请仍保持三位棚〔一〕体。”
然而,国民政府决意将东北军东调,并借此拆散“三位一体”之联盟,消除其在西北统治的巨大威胁。陈诚力主此方案。一方面,陈诚指出,缪澄流、刘多荃等愿意东调,令东北军东开不存在客观困难:“据缪澂〔澄〕流、刘多荃迭次派员称,高陵一带,大军云集,为日甚久,粮秣给养,极感困难,现已至罗掘俱穷,军民交困之境。部队本身,固立盼即日奉命东调;民众方面,亦甚望部队早日离开,若再迟延日久,深恐激成他变。同时并对东北军一二高级将领,要挟中央,壅塞下情,羁延时日,不顾前方实际情形,以自便其私图者,深致不满。窥其意亟愿直接中央,甚为诚恳。受命东开,绝无问题。”另一方面,陈诚强调,令东北军东开对于瓦解“三位一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职意西北善后,似宜从速解决,赢得时间,准备国防,较为有利。且长此拖延,非但一切因之搁置,且于所谓三位一体者,更不知何日得以解决,自然害多利少。”“今杨(杨虎城——引者注)负固三原,仍在暗中活动,以期复起”,“东北军如能次第东调,直接中央,则封建残余如杨者,必无能为也”。此外,陈诚还指出执行甲案、令东北军西开甘肃之危害:“以共党之想得渔利,杨虎城之封建野心,东北军之虚骄自大,纵一二老成谋国者,亦难有兼容并包之良策。即退一步言,纵一时接受甲案,试问如此庞大之集团,将来如何善其后?”陈诚因而建议蒋介石,“即令东北军全部,或先令刘多荃率领第一〇五、第一二九两师,缪澂〔澄〕流率领第一〇九、第一一一、第一一二、第一二〇等四师即日东开,以解其实际之苦,而坚其效顺之情。又第一〇七、第一〇八、第一一七等三师,令其东开,亦极有把握”。卫立煌亦敦请蒋介石及早下令东北军东调,“东北军大部抽调以后,西北问题迎刃而解,似未宜待杨、赤同时解决”。
事实上,蒋介石亦有将东北军东调之决心,但他认为,最好令东北军直接来电请求东调,然后再下令较妥。2月8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指示安置东北军办法,“总以调驻豫鄂皖省区为唯一方针”,但该办法“不可轻示,必须间接试探,或由东北军自动请求出此方妥,若当地环境以为未到其时,则不如暂不启口也”。蒋介石虽有将东北军调驻豫鄂皖之想法,但对于提出方式却是慎之又慎,这大概是担心,该案若由南京方面提出,会招致东北军的反对,适得其反。是时,于学忠电告麇集平、津的东北人士提供意见,王树翰、刘尚清、王树常、万福麟、刘哲、莫德惠、马占山等数十人于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甲、乙两案,决议以东调江苏、安徽两省为佳。蒋介石遂接受该建议,决定令东北军移驻豫东、皖北及苏北地区。2月14日,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到达南京,会见蒋介石,又到溪口会见张学良,最后决定改变原执行甲案的协议,将东北军西调改为东调。
经过多方力量之博弈,东北军东调成为定局。3月初,西安行营制定关于东北军移防与输送的详细计划。3月3日,东北军开始东调。驻高陵一带的五十七军徒步行军至渭南车站登车,沿陇海路东开,再南下周口、淮阳、太康一带。一〇五师移驻河南南阳,六十七军移驻安徽阜阳、涡阳。五十一军从兰州移防,先到蚌埠,不久移至苏北淮阴一带。迄至4月下旬,东北军移防完毕。骑兵军仍驻陕西咸阳,五十三军仍驻河北保定。4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特派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于学忠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为谋地方军政配合方便,国民政府又任命东北耆宿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二、 围绕整编重大原则的博弈
东北军既已东调,国民政府决定对之实行整编。在开始整编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东北军的管理方式,即由谁来统率、领导东北军?这涉及整编之重大原则。当时,存在三种可能与选择:一是放归张学良,令其继续统率东北军;二是令张学良的中意人选于学忠领导东北军;三是让东北军直隶中央,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前两种方式是继续维持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而第三种管理方式则是要取消东北军的独立性,实现军队的国家化。
对于第一种管理方式,张学良的确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透露过,希望国民政府“仍准其带东北军,即在陕甘边区训练,准备抗日”。但是,它的实现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东北军将领欢迎和接受张学良的继续领导。然而,随着张学良遭扣和二二事件的发生,东北军将领对张学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离心倾向。时已脱离东北军的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与东北军各将领密洽后得出结论:“各将领经二二事变后,对汉卿印象极坏,均不愿其回陕。”1937年2月14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称:“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可见,张学良难获东北军将领的支持。再者,张学良仍处幽禁状态,国民政府虽然在2月17日下令恢复其公职,但并没有恢复他的自由。另外,中央军将领亦有人反对让张学良重新统率东北军。例如,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即致电蒋介石,“为惩前毖后计,总望钧座睿衷独断,无论张学良如何请求,决勿再予以实际职权”。
对于第二种管理方式,于学忠曾做出过一定的努力。于学忠要求以他本人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兼统率全体东北军。他解释称,此项要求“完全为汉卿主张,然亦顾墨三在西潼会议面许何柱国者”。至于其本意,“则不有损人格的爱国条件下,关于权利地位问题,实无可无不可”。为此,于学忠拒绝按蒋介石之意带领五十一军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亲自致函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董英斌、米春霖等人,要求东北军支持他担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然而,于学忠统率全体东北军一事,实际上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东北军内部对此意见不统一,甚至存在反对声音。东北军内万福麟、刘多荃等将领对接受于学忠之统率颇有不同意见,“万寿山代表反对孝侯,而刘多荃电报亦以张出则可,否则各军各归中央可也”。于学忠虽生于旅顺,但祖籍山东蓬莱,他早年加入毅军,后入直系吴佩孚麾下,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直系势力瓦解后才投入奉系阵营。如于学忠本人所言:“我在直系为后起,在奉系则客籍。”或许是因为于学忠之出身与资历,作为东北军内元老人物的万福麟不愿归其领导。至于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他认为张学良复出,则东北军归张学良统率,否则东北军各军应归中央直接指挥。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将领表达过对于学忠的看法:“东北军将领并无拥戴于孝侯为第二领袖之必要,但对于亦无恶感,仍望中央予以相当位置,以全于之颜面,免少数人借为口实,以资挑拨。”如此,东北军在于学忠担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和统率全体东北军两事上提供的支持自然是有限度的。此外,东北军骑兵师师长郭希鹏还对于学忠谋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一事表示过反对。
其次,国民政府方面不愿批准。何应钦表示,“孝侯欲豫皖绥靖主任,且统率全东北军,两事皆难照办”。陈诚亦认为,“中央对东北军决调豫皖,并以于学忠为两省绥靖主任,何柱国为省主席……此种办法宽大乎?奖乱乎?固为顾虑赤匪,然亦不应出此”。让于学忠担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一事,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皆遇到不小阻力。4月10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称:“至孝侯任豫皖主任一节,原驻豫皖之高级将领皆不赞成。中央同人亦以赏罚不公,无以持后相责,故至今不能提出,势非变更不可。”
关于于学忠任职一事,4月14日,蒋介石与徐永昌晤谈,决定任命于学忠为江苏警备司令,驻扎江北。16日,蒋介石致电徐永昌、何应钦,建议任命于学忠为江苏警备司令兼淮海绥靖公署主任。然而,因为警备司令地位在省主席之下,须受省主席之指导,于学忠不愿担任该职,遂找人说项,设法补救,“拟请改为警备总司令或绥靖主任”。最后,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的职责权限是指挥苏北地区的驻军,而在当时,除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驻扎苏北地区外,东北军大部(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皆驻防豫皖,归刘峙指挥。由是,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之议在内外阻力下未能实现。
对于第三种管理方式,在讨论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多阻力。早在1937年2月14日,陈诚就提出整编东北军的三大原则:1.以军为单位,直隶中央;2.人事权直接归国民政府军政部;3.指挥权归行营。陈诚认为,应改变东北军一直以来“兵归将有”的军阀属性,将之整编为中央直接统率和领导的国家军队。东北军内,刘多荃亦明确主张,“过去集团形势应该打破,各军在中央指挥之下各自集中训练为正当原则”。4月20日,刘多荃、缪澄流、吴克仁向陈诚表示,“愿直接中央,不受任何人之操纵”。实际上,东北军内部对此并非没有反对意见,仍有人希望维持独立性。4月25日,东北军将领董英斌、洪钫联名致电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的东北重要人士组成的北平图存学会称:“现事迫切,极〔亟〕盼各军师长能有联衔电中央自愿禀〔秉〕公维持原案之表示,以挽时局。”他们恳请北平图存学会从事以下工作:1.联络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为东北军向中央缓颊。2.推动北平、天津各东北元老发电劝说东北军各军师长尽快表态。3.推动北平各东北团体发电劝说东北军各军师长维持独立性。然而,董英斌、洪钫的努力收效甚微,于事无补。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东北军直隶中央。
除重大原则外,对东北军之整编还涉及两个具体问题,即如何处理新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1935年10月,东北军一一〇师在陕北劳山战役中为红军所歼,部队番号遭蒋介石撤销。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成立抗日先锋队,命孙铭九为总队长、赵龙韬为参谋长,下辖3个支队。抗日先锋队官兵政治素质好,抗日热情高,与红军联系密切,因此被视为东北军的“红帽子”部队。二二事件后,董英斌告诉赵龙韬,“先锋队这个部队名称已引起内外的普遍嫉视,必须改变,省掉麻烦”,最后决定将抗日先锋队改编为新一一〇师,原3个支队改编为两个团,张政枋任师长,赵龙韬继续担任参谋长。
新一一〇师系由抗日先锋队改编而来,由东北军少壮派领导,且与中共有关联,蒋介石因而对其尤具戒心,甚为忌惮。1937年4月26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刘峙,要求对新一一〇师“特别防范,先取严密监视之布置为要”。5月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刘峙,要求“应切实准备解决部署,勿使漏网。凡对该师之各地监视部队,应切实连〔联〕系,约定特别方法,俾得时时联络,但此时切勿声张疏洩”。同日,蒋介石电告徐永昌、何应钦,新一一〇师“分子太复杂恶劣,现仍为反动宣传,而且四出挑拨,该师非彻底整顿不可”。东调后,新一一〇师配属五十一军,驻扎于皖北蒙城、蚌埠一带,蒋介石要求徐何二人嘱咐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新一一〇师“万不能调赴苏北,煽惑淮工,贻害地方”,五十一军其他各师应迅即移驻苏北,而留新一一〇师“暂驻蒙城原地勿调”。蒋介石主张,新一一〇师“即在现驻地点由中央负责处置,以免害国殃民”,如其已移动,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员督令限期解散。在蒋介石的命令到达五十一军前,新一一〇师已经随五十一军开赴苏北,驻扎睢宁。此后,于学忠将张政枋调离,并将新一一〇师官兵编入五十一军各部,引起张政枋不满。但蒋介石仍坚持解散该师的既定方针,并要求驻扎徐州、宿州的中央军第一军胡宗南部,“对睢宁准备进剿,时刻探报其情况为要”。最终,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于学忠被迫取消新一一〇师的部队番号。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一二九师。东北军一二九师原隶属驻扎于河北的万福麟五十三军,后调入陕西。东北军东调前,经蒋介石核准,一二九师配属刘多荃四十九军,万福麟对此表示不满,要求将一二九师调回河北,归还五十三军建制。5月3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致电蒋介石,提到“上年由万福麟部调二师入陕,现一师在缪澂〔澄〕流处,一师在刘处,万颇不满”,请蒋介石予以注意。然而,刘多荃颇不愿该师调回河北。他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谈话时称:“军队系国家军队,钧座如认为对华北有敷衍必要,则调归万军,如无必要,则一并整理。”钱大钧认为刘多荃“其意似不欲调回,而表面听命于钧座”。卫立煌主张一二九师应继续隶属四十九军。他向蒋介石陈述理由:“东北军服从中央,以刘、缪两军长主持最力……刘对此事(指万福麟请调一二九师回河北一事——引者注)曾表示,其部队早已归还中央,一切调遣唯钧座之命是听,其公忠体国之心昭然若揭。”一二九师各级军官对调回河北也抱有顾虑,“诚恐一旦回冀,则此后人事上必多调迁,颇呈不安之状态”。卫立煌因而请求蒋介石“仍以该师隶属刘军,维持在陕原议,以昭大信,藉慰士心”。
与卫立煌一样,刘峙、陈诚等人亦不主张一二九师归还五十三军,所不同者,他们更多是从有利于东北军整编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四十九军辖一〇五师和一二九师,共12个团,准备改编为四团制之两个师。如果一二九师归还五十三军,那么四十九军就仅剩余9个团,“编为二师不足,编为一师有余,事实上确有困难”。更复杂之处在于,一二九师归还与否还涉及东北军经费问题,“惟冀察政会补助东北军经费每月约三十万元,向由万转发一二九师,若不归还,恐宋明轩碍于寿山面子,不肯将经费拨由中央转发,则经费上又生问题”。如何安排一二九师,诚非易事。5月8日,何应钦电告蒋介石,“此事迄无两全办法,现尚在筹商中”。
关于一二九师归还万福麟问题,到5月中旬,经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缪澄流、吴克仁、刘多荃详细研讨,商妥解决办法:“各军均以十一个团编为四团制之两个调整师,万部现仅九团,而将刘军之一二九师拨两团予万,凑成十一个团之数,再由缪军拨出一团予刘,亦补足十一团。”该办法获蒋介石批准。至此,东北军整编各事商洽定妥。
三、 整编的实施与评价
国民政府依照制订计划、成立机构、召开会议等步骤实施对东北军的整编。1937年4月8日,何应钦与刘峙、陈诚、卫立煌等会商,拟定《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于次日呈报蒋介石,4月10日获蒋介石批示同意。《大纲》首先规定整理东北军的基本方针:“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主旨。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付与以较大之权能,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轨。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归,上下官兵心理安定。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根据上述整理方针,《大纲》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决定分两期对东北军进行整编。第一期是自《大纲》出台之时起至4月底止,主要任务是“确定隶属及指挥系统,各军建制、驻地及各单位经费数目与发放手续”。关于东北军的隶属及指挥系统,《大纲》要求东北军“各部以军为单位,直隶军事委员会,并受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豫皖绥靖公署之指挥”。关于东北军各军建制,《大纲》提出“暂以移防时所编配之各师而前此中央有案者为标准”。具体为:四十九军暂辖一〇五、一二九两个师;五十一军暂辖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三个师;五十七军暂辖一一一、一一二、一〇九、一二〇四个师;六十七军暂辖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七、一一五四个师。至于东北军各军驻地,仍暂时按照移防时的规定执行,即四十九军驻南阳、方城、唐河、沁阳各县,五十一军驻蒙城、凤台、寿县、颍上、霍邱、三河尖、固始各地,五十七军驻西华、商水、太康、淮阳各县,六十七军驻涡阳、太和、阜阳、临泉、沈邱各县。唯何柱国之骑兵军“候令调豫”。为强化对东北军的控制,《大纲》规定对东北军施行政治训练,“各军师恢复政治训练,由军委会政训处统筹办理”。第二期是自5月起至6月底止,按整理师编制对东北军实行整编,要求“各军均改编为两旅四团制之师二个,其实施计划由各军长拟订呈核”。
《大纲》出台以后,具体的整编工作随即展开。4月29日,国民政府成立整军机构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刘峙任主任委员,王树常、于学忠、商震、陈诚、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刘茂恩、沈克、檀自新、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胡宗南、曾万钟等任委员。5月7日,刘峙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之性质,原为军委会委员长之咨询机关,仅负整理上之建议责任,整理进行步骤,须向中央请示办理。大约将先从驻防三省之旧东北军着手。其他军队,如认为有整理必要,当次第进行。旧东北军原隶属西北剿匪总部,现该部业经裁撤,此后即直隶中央。旧东北军现有十余万之众,其编制、人事与饷章诸项,略与国军有别,此后当逐渐谋其整齐一致,使成为国家劲旅。”由此可见,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整编刚刚东调开入豫皖苏三省的东北军,并兼及三省境内其他驻军之整理。
6月1—2日,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在开封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军整编的具体事宜。会议结束后,东北军各部即遵令着手实施整编,至6月底基本完成。在编制上,“即在使之与中央采取同一之编制,俾军师长在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其权力,以增强各军之活动能力”。具体整编方法为:“依照各该军原有经费、武器、马匹,将各军一律缩编为两个师,每师四团,共计十个师,四十个团,计裁减七个师十三个团。至师属特种部队及各单位编制,均与二十六年‘调整师’编制大致相同。”
整编后的东北军采用调整师编制,每军二师,每师二旅,每旅二团。具体编制情况为: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一〇五、一〇九两个师;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一一三、一一四两个师;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一一六、一三〇两个师;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辖一一一、一一二两个师;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辖一〇七、一〇八两个师;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三、四、六三个师。经过整编,东北军被调出和被撤销的番号有:五十一军的一一八师、新一一〇师;五十三军的一一九师;五十七军的一二〇师、一〇九师;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一二九师;骑兵第二军第七师。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一〇六师、骑兵第十师、炮兵第六旅、第八旅,均另立门户。冯占海所部第六十三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九十一师番号,冯占海任师长。
东北军通过整编,从过去的军阀武装转变为国家军队,实现“国军化”。时人多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东北军的“国军化”给予好评。例如,《民声报》即发表社评《东北军“国军化”》,从军队国家化与国家近代化的视角看待东北军整编问题,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决不能有二种制度或是体系存在,尤其是军队,更非划一不可。军队必须由国家直辖,决不能属于某个人,换一句话说,全国军队都必须‘国军化’,这个国家才够得上称为近代式,不然,仍旧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混沌局面而已”。该社评将东北军“国军化”的重大意义概括为实现由“假统一”转变为“真统一”,指出“从前只是表面上的统一,现在才算真正的统一”,希望东北军“明了自己所负的特殊使命,而加紧训练,以期成为全国‘国军’的模范”。《现代评坛》亦发表简评认为,东北军遵令东调和实行整编,“不只表现了该军的决心,尤其表现了我民族复兴的征兆”,可以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全国军队实行‘国军化’的初步”。《西北论衡》也指出,东北军整编的意义完全在于“国军化”:“今日全国军队,应完全国军化,打破向昔之保有相当独立性,而东北军之能首先接受整编,为全国军队之模范,东北军将领态度之光明磊落,均足使全国国民欣慰兴奋……东北军经此整编后,能更加训练,更加充实,蔚为国家劲旅,为国家将来担负更艰重之任务,全国国民对之实抱有绝大希望。”
在国民政府的强势主导下,东北军实现整编。对于东北军将领服从整编,《中央日报》社评予以高度肯定:“旧东北军部属,莫不恪遵命令,踊跃服从,师行所至,秩序井然,人民观感,为之大变,其万福麟所部,且自动请求加入整理,其深明大义之精神,实予国人以共见,吾人于此,实不胜其佩慰。”《中央日报》同时指出东北军整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旧东北军之编制,向因历史环境种种关系,未能与其他国军一律,此不独影响国家整个国防计划,即在旧东北军自身亦不免有自外于国军之感,改良编制,实不容稍缓。”与中方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评价聚焦于东北军之整编对于实现军令统一、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同,日本方面的观察更侧重于此次整编对东北军本身的影响。《盛京时报》在报道6月初举行的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会议时强调,此次会议“于国军化之名目下,将解消旧东北军之历史的实在,与军阀的集团”。日方的态度颇值得玩味,考虑到东北军的“国军化”整编有强化国民政府抗日准备之效果,《盛京时报》的言论存在挑拨离间的意味。
东北军经“国军化”整编,发生根本性变化,褪去军阀色彩,由原来较为稳定的地方军事集团迅速蜕变为彼此独立而直隶中央的数支军队。东北军的这种蜕变,“有利于国民政府消除地方主义和强化中央集权”,“使得南京政府在筹划抗战方略时少了一支地方势力的牵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但是,若从东北军本身的发展历史而言,西安事变后的“国军化”过程则是喜忧参半、利弊并存的事情。“国军化”从观念上消弭了东北军的乡土属性,进而割裂了东北军与东北地域的情感纽带。正是由于“国军化”,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东北军不复存在,“从此,东北军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当然,作为实体意义上的东北军依然存在。整编结束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北军迅即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开始了新的征程。
结 语
“整军即所以抗日”,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军实行整编是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内部抗日力量整合的一个缩影。早在1937年1月,蒋介石就把“积极整军,继续建立国防,强化军力”作为当年对内方针列入年度大事表。为实现“平定西北,安定西南”,蒋介石思考“东北军之切实统制”和“川军之改造与统制”两大问题。依此,国民政府相继对东北军和川军两大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整编。相较而言,对东北军之整编呈现出更多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首先,对国民政府而言东北军是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叛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之联盟短期内仍然存在,国民政府欲实现对东北军的整编,必须设法拆散“三位一体”联盟,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然而,“三位一体”内部,中共和杨虎城均希望东北军继续留在西北,东北军内部少壮派亦持同样主张,将东北军东调实际上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困难。但是,随着二二事件的发生,形势急转,东调得以实现。
其次,国民政府对东北军的整编,既涉及将其直隶中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也牵涉对东北军个别部队的处置与安排。对于直隶中央,东北军内部存在反对声音,但国民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且刘多荃、缪澄流等东北军元老均赞成直隶中央。在整编过程中,如何处置与安排新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一度成为问题。在蒋介石的强硬要求下,新一一〇师被解散,一二九师经东北军各将领协商,获得妥善安置。
西安事变后的“国军化”整编使东北军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整编后,东北军改变地方实力派的属性,实现军队的国家化,以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观之,这大大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当时中国社会舆论普遍对东北军的整编给出积极评价,直接反映出西安事变后,对内团结息争、对外抗日御侮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影响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
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军的整编固然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但亦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整编过程中,刘多荃、缪澄流等元老派地位上升,张政枋等少壮派受到打压。二二事件后,元老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疏离,增加了战时中共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困难。整编后,东北军的人事、经费、政工等完全归国民政府掌握,实际上强化了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抗战中后期国共摩擦与斗争剧增,东北军很难维持超然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乃至消亡。